溢出:中國制造業供應鏈的危與機
http://www.gjzbw99.com 2022-08-17 14:41 來源:
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爭端的加劇與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供應鏈“脫鉤”的話題漸熱。無論是特朗普掀起制造業回流的旋渦,或是拜登重塑產業鏈的計劃,還是疫情影響下層出不窮的生產外遷現象,每一次的轉移沖擊都使得中國制造業供應鏈“脫鉤”的言論甚囂塵上。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供應鏈轉移?中國制造業受到何種供應鏈轉移沖擊?謹以此文探討產業轉移現象下中國制造業供應鏈溢出的危險與機遇。
一、無法回避的溢出
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發展,企業為保持和提高競爭優勢,綜合評估各地區資源優勢并將部分或全部生產環節,大體沿襲著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路徑進行外遷,亦稱之為產業轉移。產業的轉移必然導致供應鏈的溢出,我們可以從全球產業轉移的歷史來一窺世界供應鏈網絡的發展變遷。
多數分析認為:從第一次工業革命至今,全球完成了四次大規模、大范圍的產業轉移,每一次的持續時間約20-30 年,并且當前正處于第五次產業轉移的浪潮之中。
第一次產業轉移發生于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率先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并一躍成為當時“世界工廠”的英國,面臨著產業容量日漸飽和產業成本不斷攀升的問題,在18世紀末逐步開始向西歐大陸和北美地區進行產能和工業革命科技成果輸出,法國、德國、美國等國家成為主要承接國。其中,美國憑借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開放的經濟政策成為了本次產業轉移中的最大受益者,并于19世紀60年代主導了以電器廣泛應用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迅速崛起并超越英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和全球供應鏈網絡中心。
第二次產業轉移發生于20世紀50—60年代。1945年二戰結束后,美國主導了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第三次科技革命”,促進了美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汽車、化工等資本密集型產業成為主要發展產業,紡織、鋼鐵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向聯邦德國、日本轉移,并使日、德兩國成為全球經濟強國和主要供應鏈網絡中心。
第三次產業轉移發生于20世紀70—80年代。與英美的發展路線一樣,日德同樣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的挑戰,并開始將輕工業、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型產業向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韓國的“亞洲四小龍”轉移,造就了一批新興的東亞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主要供應鏈網絡中心。
第四次產業轉移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2012年。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及“亞洲四小龍”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此次產業轉移中,中國憑借著顯著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優勢,廣闊的國內市場需求和改革開放的良好政策逐漸成長為新的“世界工廠”和主要供應鏈網絡中心,并建立起了全球最完備的產業體系。
當前,全球正處于第五次產業轉移的浪潮之中。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了絕對下降,到達“劉易斯拐點”。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生產成本的提升和發達國家“制造回歸”、“再工業化”政策的提出,疊加新冠疫情常態化影響,中國承受著高端制造業向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回流以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東南亞等欠發達國家加速轉移的“雙向擠壓”。
我們可以看出,數次的產業轉移使得世界制造中心不斷變化,而全球供應鏈網絡也隨之不斷重構。中國作為第四次產業轉移的主要承接國,沿著既定的產業發展規律,和英美日德等老牌工業化國家一樣,在接收低附加值產業的同時不斷升級產業結構,并接受著第五次產業轉移與供應鏈溢出的考驗。
二、新興崛起的對手
隨著第五次產業轉移浪潮的愈演愈烈,下一個世界工廠的落點尤為引人關注。目前來說,關于本輪產業轉移主要輸出地——下一個世界工廠,目前風頭正盛的是越南與印度。
在產業轉移初期,產業輸出國往往會向產業承接國輸出投資,產業承接國往往會向產業輸出國出口最終商品。因此,出口與FDI(外國直接投資)是衡量一個國家全球工業地位與發展前景的重要指標。
(一)出口
1、出口規模
CEIC Data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出口總額約2.14萬億美元,同期越南出口總額1765.6億美元,印度出口總額2644.2億美元。2021年,中國出口總額約3.37萬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了57.6%;同期越南出口總額3361.0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了90.4%,2021年越南GDP總值3626.37億美元,出口占GDP比重高達92.7%;2021年印度出口總額達到了3954.7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了49.6%,2021年印度GDP總值30841.8億美元,出口占GDP比重為12.8%。
可以看出,2016-2021年,越南出口規模增勢強勁;而印度出口規模增幅雖然不及同期中國,但印度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出口計劃,未來五年,他們希望在電子行業的各個領域實現百倍的提升。同時,2022年3月和4月份,印度首都的英迪拉-甘地機場已經連續兩個月超過中東大亨迪拜,成為全球第二繁忙的機場。
2、出口結構
越南的優勢產業集中在紡織服裝、電子和機械設備等制造領域。越南電子設備行業出口份額位列世界第7,擁有包括三星、富士康、佳能、LG等全球知名電子廠商生產基地。而越南紡織服裝制造業已具備成熟的規模與完善的產業鏈結構,位居全球前列。特別是在中國受奧密克戎疫情影響的背景下,越南紡織服裝出口有著明顯增長。越南紡織服裝協會主席武德江在2022年6月21日由越南紡織服裝協會與美國國際棉花協會(US.Cotton)聯合舉行的可持續棉花供應鏈研討會上表示,今年前六個月越南紡織服裝出口額估計約為220億美元,同比增長23%。
印度的優勢產業集中在化工產品、礦產品和貴金屬及制品,但近年來,電子與汽車等行業不斷發展,且是政府大力推進的方向。
Invest India數據顯示,2020年財年印度電子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2.7%,出口117億美元。2021年,印度移動手機的產值達3000萬美元,產量從16年占全球份額的8.7%上升至15.5%。印度不僅有龐大的手機市場,還匯聚了以蘋果為首的美國手機企業和以三星、索尼為首的日韓手機企業。截至目前,三星在印度設有兩家工廠、五個研發中心和一個設計中心,擁有近2萬家零售店;蘋果三大供應鏈合作伙伴富士康、和碩以及緯創已承諾未來5年投入近9億美元,用于擴大對印度的投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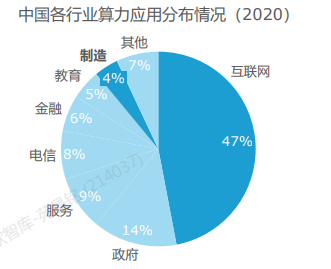
圖 各國手機產量占全球總產量份額變化
Invest India數據顯示,目前印度的汽車工業價值超過2220億美元,占印度GDP的7.1%,占印度出口總值的8%。預計到2030年,印度汽車工業將成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工業。其中,新能源汽車是印度政府想要實現彎道超車的重點方向,目前豐田、鈴木、比亞迪和寶馬都正在印度建立新能源汽車零部件或整車制造工廠,印度政府也在積極同特斯拉進行建廠合作溝通,盡管目前雙方在關稅上分歧較大。彭博社預計,到2040年,中國新車銷售中,77%將是電動汽車,而印度這一比例將追趕至53%。
(二)FDI(外國直接投資)
CEIC Data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FDI為1747.5億美元,同期越南FDI為126億美元,印度FDI為444.6億美元。2021年,中國FDI為3339.8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了91.1%;同期越南FDI為388.5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了208.3%;印度FDI為836億美元,較2016年增長了88%。
《經濟學人》智庫(EIU)2021年1月發布的越南的專題報告中指出,在接下來的十年內,越南仍將是亞太地區最具競爭力的制造基地之一,越南吸引的外資水平占GDP 6%以上,是新興經濟體中比例最高的國家。印度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其龐大的消費市場,這也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來,印度政府也在積極謀求外資的引進與跨國并購工作。
無論是從出口還是FDI來看,越南的發展速度的確令人驚嘆,印度雖然不及越南,但數據同樣較為可觀。后起之秀,不可否認地會給中國制造業帶來沖擊。特別是在2022年春,中國制造業受奧密克戎疫情造成的供應鏈中斷影響,越南與印度的出口大幅增長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中國制造業的替代作用。
三、溢出之危與機
越南,毗鄰中國,擁有良好的勞動力素質(同處儒家文化圈,群眾有良好的儲蓄意愿)、堪稱夢幻的人口結構( 近億人口,32.9歲的平均年齡)、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數量眾多的優良港口、更為優惠的關稅政策,這都使得越南的出口加工業極具競爭優勢,制造與出口規模連年攀升。但越南受限于其相當于中等規模勞動力與產值供給,盡管近年來發展迅猛,長遠來看并不具備可以完全承接中國供應鏈的能力。
印度,擁有比肩中國的人口規模、更為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廣袤的市場腹地、趨于完善的電子產業鏈、更為發達的軟件信息產業以及與歐美接軌的語言能力等,這些都是讓印度初步具備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的良好資質。雖然印度的基礎設施條件不甚良好,且社會、宗教環境復雜,但近年來,印度政府政策頻出,特別是從“中國產業替代政策”中可以明顯看出改善與激勵,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國制造”的雄心。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2年印度GDP增速為8.2%,且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將持續高于中國。
但是,制造業加速向越南和印度轉移,某種程度上來說,對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齊全的工業體系與供應鏈網絡,也擁有最大規模的市場,在制造業轉移空心化的風險面前也并不是脆弱得不堪一擊。中國制造業在如何在面臨越南、印度等國家制造規模不斷擴張的危機同時維持自身競爭優勢并實現制造出口規模的穩步增長,已成為應對溢出風險的關鍵所在。制造企業應深入推進數字化轉型與智能制造,借助數字技術驅動生產、研發、運營與管理模式的變革,拓展技術研發創新的能力、生產方式變革的能力以及組織管理再造的能力,從而全面提升研發、生產、運營、管理等業務環節的效率,實現企業商業模式和價值體系的重構,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同時,制造企業應加速向服務化轉型以發展企業的“第二增長曲線”。企業從低附加價值領域的生產、組裝環節向高附加價值領域的產品研發、售后等服務環節不斷延伸,占據產業鏈高附加價值環節,如此也就無需再過分擔憂產業里中低端加工制造環節的轉移與供應鏈溢出了。正如2021年《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超越生產》中指出,附加值越來越多的產生于制造業之外,不僅要從制造業生產的角度來看待全球價值鏈,還要從要素收入角度的無形資產、數字平臺、知識產權等生產以外的服務貿易來看待全球價值鏈。例如以要素收入衡量貿易,美中貿易逆差較商品差額減少了三分之一。
此外,全球化經濟環境下,國家之間的關系是競爭與合作并存。印度2021年從中國進口突破975億美元,創出新高,約占其進口總額的17%;而越南進口總額的33%來自中國內地。在中國制造業外遷的過程中,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拓疆之旅。例如,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企業因為勞動力成本、關稅等方面的考慮,紛紛主動在越南、印度等國家投資建廠生產或轉移中成品組裝環節進行轉口貿易,這也意味著以中國為中心的制造業供應鏈網絡規模在不斷擴大,中國制造企業正在通過生產外遷的方式不斷尋求更加優化的發展路徑與機遇。
如果說供應鏈溢出是無法回避的客觀規律,那么疫情、地緣政治沖突等都只是加速中國制造業轉移的助推器。誠然,憂患意識是企業生存發展不可缺少的文化精神,但企業也更應當看到危險背后的機遇,汲取轉危為機的勇氣,審慎對待制造業供應鏈的轉移,加速推進數字化轉型與智能制造,積極向服務型企業邁進,謀求發展自身核心競爭優勢以增強應對外部危機的能力。




